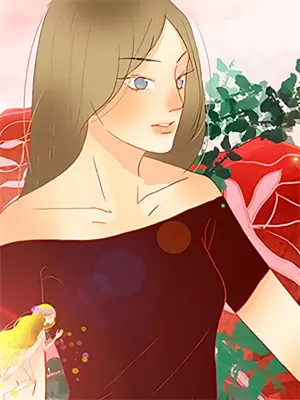- 我死后,守护我的蛇妖魂飞魄散
- 分类: 其它小说
- 作者:爱吃冬瓜的瑜
- 更新:2025-08-26 18:41:30
《我死后,守护我的蛇妖魂飞魄散》精彩片段
七岁那年,我从火场爬出来,怀里抱着一条快死的黑蛇。 它说:“你救我,我护你一生。
” 可没人知道,那晚火场里,有两个影子——一个是七岁的我,另一个,是蛇,还是人?
二十年来,它替我挡灾、改命、续命,流的血是黑的。 可最近,它开始消散,
像灰烬被风吹走。 而我的记忆里,多了不该有的画面—— 我才是那个,先开口许诺的人。
这次,换我烧了伞,焚了契,护它一程。 哪怕代价是,揭开我根本不该存在的真相。
1我叫林晚,25岁,广告公司打工人,月薪税后九千八,房租四千五,剩不下几个钢镚儿。
但今天,我差点被一个穿高定的男人砸晕。凌晨一点,暴雨像天上谁掀了缸,哗啦啦往下倒。
我缩在写字楼门口,等着雨停。手机电量1%,连个网约车都叫不动。忽然,
一把黑伞从天而降。我没抬头,只看见一双锃亮的黑色牛津鞋,裤线笔直。再往上,
是修长的腿,挺括的风衣下摆,最后是一张脸——眉骨高,鼻梁直,眼窝深得像刀刻的,
嘴唇薄,他面无表情的开口。“你忘了我,”声音低得像是在说悄悄话,“但是我记得你。
”我往后退半步,高跟鞋一滑,差点摔个狗吃屎。他伸手扶我,指尖碰到我手腕那一瞬,
我鸡皮疙瘩全起来了。凉,特别凉,像死人一样没有什么温度。“神经病啊?”我甩开他,
“要发疯去别处发。”他没动,就那么站着,伞也不收,雨水顺着伞骨流进他领口,
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“7岁那年,你老家山洪暴发,你冲进泥石流,
从烧塌的柴堆里抱出一条快死的黑蛇。”他盯着我,眼神像要把我钉死在墙上,
“那条黑蛇就是我。”我冷笑:“哦,那你是不是还得谢谢我?要不现在给我磕一个?
”他忽然抬手,指尖轻轻划过我左肩。那一瞬间,我像被烙铁烫了。肩胛骨那道蛇形疤,
炸了。疼得我眼前发黑,差点跪下去。他扶住我,声音更轻:“你给我的银夹,还在你发间。
你救我时说:‘小蛇你别怕,这次我来保护你,以后你也要记得保护我哦。’”我浑身发抖。
那句话……是我从小到大,每次做噩梦都会说的呓语。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?
”我声音都劈了。他松开手,把伞塞进我手里:“沈夜。来还债的。”说完,转身就走,
背影没入雨幕,像一滴墨汁融进黑水里。我愣在原地,手里攥着那把伞——檀木柄,
蛇首雕头,很沉。第二天早上,我顶着黑眼圈进公司,前台小妹眼睛一亮:“林晚!
有人等你!”我抬头。沈夜坐在大堂沙发上,一身黑色西装,袖扣是两粒黑曜石,
手里端着一杯热美式。他看见我,起身,递过来:“你喝美式,不加糖。
”我盯着他:“你跟踪我?”“不用跟踪。”他淡淡道,“你每天七点二十三分进电梯,
八点零七分打卡,午休吃沙拉,下午三点喝咖啡,加班到九点四十五分。”他顿了顿,
“昨晚你做了三个梦,最后一个,梦见我烧死了。”我头皮炸了。“你他妈到底想干嘛?!
”“护你。”他看着我,眼神像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的古董,“你救我一次,我护你一生。
这是命契。”“放你妈的狗屁!”我甩手把咖啡泼在他鞋上,“我不认识你!再跟着我,
我报警了!”他低头看了看鞋,没生气,反而笑了下:“好。”然后转身走了。
我以为这事完了。结果晚上回家,公寓门口放着一把伞。——和昨晚那把,一模一样。
我手抖着拿起来,翻到伞骨内侧,一行小字刻着:“赠晚晚,七岁生日快乐。
——母”我脑子嗡的一声。这把伞,是我七岁那年生日我妈送的。山洪那年,老屋烧了,
它早该化成灰了。我冲进屋,翻出相册。照片里,我撑着这把伞,笑得傻乎乎的。
手机突然响了。陌生号码,一条语音。我点开。沈夜的声音,
低得像在耳边呢喃:“你救我那夜,屋顶塌了,你被砸晕。我把你拖出来,自己被压在梁下,
烧了三天才断气。 我魂不散,等你醒来。 可你失忆了。 我守了你18年,才敢现身。
”“你每活一天,我就多受一分魂火焚身之苦。” “你救我时,许的是‘一生’。
我若不还,魂飞魄散。”“所以……” “我不怕你死。” “我怕你死得太早,
我还不了债。”语音结束。我瘫坐在地,手里攥着伞,肩上的疤又开始隐隐作痛。窗外,
雨又下了起来。我抬头,看见对面楼顶,一道黑影静静站着,撑着伞,望着我的窗户。
像一座守墓的石像。我抓起伞,冲到窗边大喊:“你到底想怎么样?!”风大雨大,
可那声音,还是清晰地传了过来:“我想你活着,但不是为了你,是为了还债。
”我愣在原地。雨夜里,他缓缓转身,消失在黑暗中。只剩那把伞,死死攥在我手里,
就像攥着一段我不记得的命。2沈夜从那天起,就成了我工位外三米处的固定装饰。
每天早上七点二十三分,他准时出现,一身黑,像刚从殡仪馆下班。不说话,就站着,
目光落在我头顶三寸,仿佛在数我掉了几根头发。同事小美第一天看见他,
还装模作样夸一句:“林晚,你这男朋友气质真绝,像电影里走出来的。
”我冷笑:“他是来收尸的,不是来谈恋爱的。”她翻白眼:“装什么清高,
不就是找了个金主嘛?”我没理她。可第二天,全公司都知道我“靠男人上位”了。
导火索是王总。那天开方案会,王总拍桌:“林晚,你这创意太水!重做!
”我刚要开口解释,会议室门被推开。沈夜走了进来。他没看我,径直走到投影前,
手指一点屏幕:“贵公司上季度虚报营收三百万,税务稽查已立案。若不想明天上热搜,
建议闭嘴。”王总脸都绿了,会议草草结束。回到工位,主管把我叫进办公室:“林晚,
你是不是找人威胁客户?”我愣住:“我没有!”“没有?”主管冷笑,
“那你这位‘朋友’怎么知道王总的事?”我哑口无言。中午吃饭,
小美在茶水间阴阳怪气:“某些人,方案做不好,就找金主出头,真当公司是夜总会呢?
”她朋友圈随即更新:“靠男人吃饭的,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” 配图是我和沈夜的背影,
文字P上“靠男人上位的婊子”。评论区炸锅:“难怪她升得快”“长得还行,
能理解”“建议查查她和老板有没有关系”。我气得发抖,
抓起手机给沈夜打电话:“你以后别来公司!”电话接通,他声音低沉:“昨晚,
你本该被王总推下楼梯。”我愣住。“他喝多了,在消防通道堵你,想动手。”沈夜淡淡道,
“我替你挡了。”“所以你就用威胁客户的方式‘救’我?!”我压低声音,
“你现在是救我,还是毁我?!”他沉默两秒:“你想要平安,还是清白?”我挂了电话,
手抖得像帕金森。那天晚上,我又梦到了山洪。小女孩冲进火场,
从柴堆里抱出一条焦黑小蛇。蛇眼睁开,竟是人瞳,流泪,泪滴成银。
女孩哭着说:“你活下来,就要护我。”突然,屋顶塌下,火焰吞没一切。我惊醒,
冷汗浸透睡衣。抬手摸肩,指尖一湿——肩上那道蛇形疤,渗出一滴墨血,黑得发亮,
像蛇爬过的痕迹。我冲进浴室,用指甲狠狠刮擦疤痕,无感。可当我默念“护我一生”时,
整条左臂瞬间麻木,像被蛇缠住,动弹不得。我瘫坐在地,盯着那滴墨血,
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:这伤,是真的。第二天,我请假回老家。我翻看城建档案,
老屋2000年因火灾重建,图纸标注:“存有未知生物残骸,建议封存。”我租了铁锹,
挖开废墟。三小时后,铲子碰到硬物。——一具巨大蛇骨,长约三米,肋骨断裂,脊椎扭曲。
最诡异的是,断裂的肋骨间,嵌着一块银片,形状很像我发夹的缺口。我颤抖着拍照,
银片突然渗出墨血,顺着雨水流进土里。当晚,我刚进公寓,门铃响了。沈夜站在门外,
浑身湿透,像从水里捞出来。我把照片甩他脸上:“这是你?!”他盯着照片,眼神悲恸,
手指轻抚银片位置:“你救我那夜,老屋的屋顶塌了,你被砸晕过去。
我想尽办法把你拖出去来,尾巴却被压住,烧了三天才断气。我魂一直不散,等你醒来,
你却失忆了。我守了18年,现在才敢现身。”我崩溃:“那你现在是要报恩?
”他摇头:“是还命。”“你救我一次,我护你一生——但护的不是你的平安,是你的死期。
”我脑子嗡的一声:“什么意思?”他抬眼,瞳孔深处墨色流动:“命契规定,
我必须替你承受所有灾劫。”“所以……你每次出现,都是因为我快出事了?”“对。
”我毛骨悚然:“你……你到底是什么?”他抬手,指尖划过我颈侧,
凉得像蛇信:“你救的,是一条……等了你18年的债。”我忽然问:“如果……我死了呢?
”他眼神一颤:“那你欠我的,就永远还不清。”“我会永困人间,不得轮回。”我愣住。
他转身,消失在夜色:“所以,林晚……你最好别死。”我回到公寓,取下发夹。
银夹背面裂痕扩大,渗出更多墨血。我滴一滴水上去,液体瞬间吸收,银夹微微发烫。
手机自动亮起——浏览器历史显示,
我昨夜无意识搜索了:“山洪火灾 2000年 7月15日”。我盯着银夹,
轻声问:“你……是不是也在疼?”窗户对面,沈夜缓缓抬起手,隔着雨幕,
做了个护住心口的动作。然后,转身消失。我攥紧银夹,肩上的疤,又开始隐隐作痛。
3今天我出门时,楼上装修,掉下来一块瓷砖,沈夜替我挡下了。沈夜的骨头,
是真他妈的硬。医院X光片出来,医生把我拉到走廊,压低声音:“林小姐,
你男朋友这伤……不正常。”我盯着片子:“怎么了?”“冲击力是常人三倍,
而且……”他指着骨骼边缘,“你看这纹路,像不像鳞片?”我没说话。那天晚上,
我偷看了他的病历——“非人类钙化特征”,七个字,像刀刻进我眼里。他躺在病床上,
手臂打着石膏,脸色白得像纸。我坐在床边,指甲掐进掌心。“疼吗?”我问。
他摇头:“不疼。”我鼻子一酸,差点又哭出来。这人怎么这么能扛?魂都快烧没了,
还在这装深沉。“所以你是说,”我咬牙道,“我每活一天,你就得多受一份罪?”他抬眼,
瞳孔深处墨色流动:“对。”“那我不活了行不行?你走吧!”他忽然笑了,
笑得我心口发紧:“你若死,命契不破,我仍永困人间。所以……你必须活着,
哪怕……活得痛苦。”我愣住。这逻辑怎么这么操蛋?我救他,结果变成他永生永世的牢笼?
第二天,公司团建。小美“好心”给我夹菜:“林晚,这鱼新鲜,你尝尝。
”我盯着那块白肉,突然想起沈夜的话——“他们开始动手了。”我夹起鱼,
不动声色倒进桌下的包里。饭吃到一半,我假装去洗手间,把鱼倒进马桶冲了。回来时,
小美眼神闪了闪。半小时后,我肚子开始疼。不是饿的,是像有人拿刀在胃里搅。
我冷汗直冒,眼前发黑。沈夜冲进来,一把扣住我手腕,另一手按在我胃部。我猛地呕吐,
吐出一滩黑血。他踉跄后退,嘴角也渗出黑血。“河豚毒素。”医生脸色发白,
“剂量够死三个人。”沈夜躺在隔壁床,虚弱道:“我替你受了七成。
”我抖着问:“小美……她怎么会……”他闭眼:“不是她。是‘焚蛇会’。”“什么会?
”“当年烧死我的人,信的邪教。”他声音轻得像风,“他们怕我回来,更怕你活着。
”我浑身发冷。当晚,我又梦到山洪夜。但这次,我看清了——一群黑袍人围着火堆,
兴奋的喊着:“焚尽异类,净我人间。”火堆下,一条黑蛇被铁链锁住,鳞片焦黑。
小女孩冲出人群,砍断铁链,抱起蛇。黑袍人怒吼:“她是‘护蛇者’!烧了她!”我惊醒,
肩上疤痕裂开,渗出墨血。镜中,我发间的银夹,自动旋转了180度,蛇首朝下。
我盯着它,轻声问:“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?”第二天,电梯出事。晚上下班,我按了B1,
电梯突然失控,急速下坠。我尖叫,沈夜撞开电梯门,将我推出,自己被卡在断裂钢缆间。
救援队说:“配重块被人腐蚀,是人为的。”沈夜全身多处骨折,送医时已失血过多。
手术室外,医生递给我一块从他肋骨间取出的金属片——刻着蛇形图腾,
和我梦里黑袍人的徽记一模一样。我攥着那块铁片,手抖得像帕金森。回到病房,
沈夜昏迷着,唇色发灰,体温低得像冰。我抓着他的手:“你醒醒!你他妈给我醒醒!
”他眼皮动了动,睁开一条缝:“再三次……我就没了。”“什么三次?
”“替你挡劫……只剩三次机会。”他声音微弱,“再三次……魂就烧光了。
”我崩溃:“那我不活了!你走吧!让我死!”他苦笑:“你死了也没用,命契不破,
我仍困在这人间。所以……你必须活着。”我愣住。这操蛋的命契,怎么死都死不了?
我忽然冷笑:“行,你不让我死,那我来猎他们。”当晚,我在公司群发消息:“今晚加班,
沈夜来接我。”我知道“他们”会来。果然,十点,我躲在消防通道,听见机房有动静。
我冲出去,一个黑影戴着面具,手持刻有蛇图腾的刀,正摆弄电梯线路。“找我?”我冷笑。
他转身,刀光闪过。沈夜及时出现,一脚踢飞刀,与对方搏斗。黑影逃走,
留下一枚徽章——“焚蛇会·守火人”。我攥着徽章,冷笑道:“这次,换我猎你们。
”回到病房,沈夜伤重,靠在床头,
声音微弱:“林晚……你有没有想过……为什么他们要杀你?”我愣住。他抬手,
指尖轻触我心口:“因为你救我那天,不只是救了我。你打破了‘焚蛇会’的千年诅咒,
你是‘护蛇者’,他们的天敌,所以……你活着,就是最大的灾劫。”我浑身发冷。
他闭眼:“而我护你……就是在护一个,本该被烧死的世界。”4李浩出现在公司门口那天,
我正啃着冷掉的三明治。他穿着我送他的那件灰风衣,头发乱糟糟的,
像条被雨淋透的流浪狗。“林晚,复合吧,我错了。”他声音发抖,“我知道你现在有别人,
可他能给你什么?我至少……至少知道你喜欢什么牌子的卫生巾。
”我差点把三明治吐他脸上。“你脑子被门夹了?”我冷笑,“分手是我提的,
因为你偷看我手机还删我工作群!”他眼神一暗:“可你现在交往的这个男人……他不是人。
”我皱眉:“你说谁?”“穿黑衣服那个。”他压低声音。我浑身一冷。那天晚上,
我收到李浩短信:“照片我已发到三个大群里了,想我删照片可以,除非你复合。
”配图是我大学时的私密照,角度暧昧,一看就是偷拍的。我气得手抖,正要打电话骂他,
手机突然响了。是李浩的语音。点开,他的声音发颤,
像被掐住喉咙:“林晚……别惹他……他不是人……”“谁?!”他不回。半小时后,
他朋友圈更新:“别惹穿黑衣服的,他不是人。” 配图是家门口——一把黑伞靠在门边,
伞柄蛇首雕头,正对着猫眼。伞,和我那把一模一样。第二天,李浩删号跑路,公司辞职,
老家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。我冲到楼下,踹开沈夜的房门。他坐在黑暗里,一身黑衣,
像从夜色中长出来的。“你对李浩做了什么?!”我吼。他抬眼,
最新章节
同类推荐
猜你喜欢
 此后星沉溺深海夏浅浅霍砚完结好看小说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此后星沉溺深海(夏浅浅霍砚)
此后星沉溺深海夏浅浅霍砚完结好看小说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此后星沉溺深海(夏浅浅霍砚)
可爱猫
 我死后,冷情妻子却疯了(林羽许如烟)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我死后,冷情妻子却疯了(林羽许如烟)
我死后,冷情妻子却疯了(林羽许如烟)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我死后,冷情妻子却疯了(林羽许如烟)
可爱多
 爱意蒙尘(秦琳周昊)热门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大全爱意蒙尘秦琳周昊
爱意蒙尘(秦琳周昊)热门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大全爱意蒙尘秦琳周昊
可爱多
 安安洛雪《台风时妻子选择救男保姆的狗后,悔疯了》全文免费阅读_台风时妻子选择救男保姆的狗后,悔疯了全集在线阅读
安安洛雪《台风时妻子选择救男保姆的狗后,悔疯了》全文免费阅读_台风时妻子选择救男保姆的狗后,悔疯了全集在线阅读
可爱多
 人生若无爱(江若禾冉轻芸)最热门小说_全本完结小说人生若无爱(江若禾冉轻芸)
人生若无爱(江若禾冉轻芸)最热门小说_全本完结小说人生若无爱(江若禾冉轻芸)
可爱多
 季长鸣聂云依(救回徒弟后,我倒赔一个女友)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救回徒弟后,我倒赔一个女友最新章节免费阅读
季长鸣聂云依(救回徒弟后,我倒赔一个女友)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救回徒弟后,我倒赔一个女友最新章节免费阅读
可爱多
 调换体检报告后,总裁妻子倾家荡产洛辰楚瑶小说完结_免费小说全本调换体检报告后,总裁妻子倾家荡产(洛辰楚瑶)
调换体检报告后,总裁妻子倾家荡产洛辰楚瑶小说完结_免费小说全本调换体检报告后,总裁妻子倾家荡产(洛辰楚瑶)
可爱多
 林安然陆司年(困在旧日回廊)全集阅读_《困在旧日回廊》全文免费阅读
林安然陆司年(困在旧日回廊)全集阅读_《困在旧日回廊》全文免费阅读
可爱猫
 老公装穷后,我让他真的穷了(何念周淮安)阅读免费小说_完本热门小说老公装穷后,我让他真的穷了何念周淮安
老公装穷后,我让他真的穷了(何念周淮安)阅读免费小说_完本热门小说老公装穷后,我让他真的穷了何念周淮安
清风不在
 旺妻圣体的我离婚后,总裁妻子人财两空裴澈林嫣最新更新小说_在线阅读免费小说旺妻圣体的我离婚后,总裁妻子人财两空裴澈林嫣
旺妻圣体的我离婚后,总裁妻子人财两空裴澈林嫣最新更新小说_在线阅读免费小说旺妻圣体的我离婚后,总裁妻子人财两空裴澈林嫣
一毛三
 政王本王穿越到大雍成国师后,成了摄政王的白月光全文免费阅读_政王本王完整版免费阅读
政王本王穿越到大雍成国师后,成了摄政王的白月光全文免费阅读_政王本王完整版免费阅读
书信
 车被偷走后,保姆对我大打出手(诸葛肥龙刘素兰)免费小说笔趣阁_完结版小说推荐车被偷走后,保姆对我大打出手(诸葛肥龙刘素兰)
车被偷走后,保姆对我大打出手(诸葛肥龙刘素兰)免费小说笔趣阁_完结版小说推荐车被偷走后,保姆对我大打出手(诸葛肥龙刘素兰)
诸葛肥龙
 《老婆和男秘书纠缠不清,我让他们火遍全网》江淮之赵淑宁火爆新书_老婆和男秘书纠缠不清,我让他们火遍全网(江淮之赵淑宁)最新热门小说
《老婆和男秘书纠缠不清,我让他们火遍全网》江淮之赵淑宁火爆新书_老婆和男秘书纠缠不清,我让他们火遍全网(江淮之赵淑宁)最新热门小说
清沐
 宋莹莹陆修言《老公和秘书暧昧不清,我让他们火遍全网》全文免费阅读_老公和秘书暧昧不清,我让他们火遍全网全集在线阅读
宋莹莹陆修言《老公和秘书暧昧不清,我让他们火遍全网》全文免费阅读_老公和秘书暧昧不清,我让他们火遍全网全集在线阅读
清沐
 和妻子互送惊喜后,我和她反目成仇谭诚苏白玉小说完整版免费阅读_热门小说排行榜和妻子互送惊喜后,我和她反目成仇(谭诚苏白玉)
和妻子互送惊喜后,我和她反目成仇谭诚苏白玉小说完整版免费阅读_热门小说排行榜和妻子互送惊喜后,我和她反目成仇(谭诚苏白玉)
西北射天狼
 苏莹莹谭铮(我供养的男友为新欢抽我耳光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(我供养的男友为新欢抽我耳光)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
苏莹莹谭铮(我供养的男友为新欢抽我耳光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(我供养的男友为新欢抽我耳光)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
西北射天狼
 和妻子的男闺蜜玩剧本杀后,我选择离婚(陈冬江软软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和妻子的男闺蜜玩剧本杀后,我选择离婚全文阅读
和妻子的男闺蜜玩剧本杀后,我选择离婚(陈冬江软软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和妻子的男闺蜜玩剧本杀后,我选择离婚全文阅读
乙叶
 于悠悠林川丈夫赶去参加青梅葬礼成为植物人后,我和女儿不要他了完结版在线阅读_丈夫赶去参加青梅葬礼成为植物人后,我和女儿不要他了全集免费在线阅读
于悠悠林川丈夫赶去参加青梅葬礼成为植物人后,我和女儿不要他了完结版在线阅读_丈夫赶去参加青梅葬礼成为植物人后,我和女儿不要他了全集免费在线阅读
八个元宝
 太子弃我之后想去母留子,却被我的真正身份吓疯了(登基大王蓉蓉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《太子弃我之后想去母留子,却被我的真正身份吓疯了》登基大王蓉蓉免费小说
太子弃我之后想去母留子,却被我的真正身份吓疯了(登基大王蓉蓉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《太子弃我之后想去母留子,却被我的真正身份吓疯了》登基大王蓉蓉免费小说
血糕
 苏君诚周晚霞(老婆疯了非要和宠物结婚,我选择离婚)全集阅读_《老婆疯了非要和宠物结婚,我选择离婚》全文免费阅读
苏君诚周晚霞(老婆疯了非要和宠物结婚,我选择离婚)全集阅读_《老婆疯了非要和宠物结婚,我选择离婚》全文免费阅读
_小当家